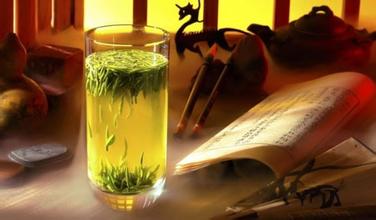书山拾翠――品茗诗话
2009-08-11 14:44
来源:中国茶道网 作者:佚名
喝茶在我国形成习俗很早,在汉代的典籍中就有“烹茶尽具”的记载。唐代隐士陆羽嗜饮茶,著《茶经》三篇,言茶之源流、饮法、茶具甚详,被后世奉为“茶神”。

喝茶在我国形成习俗很早,在汉代的典籍中就有“烹茶尽具”的记载。唐代隐士陆羽嗜饮茶,著《茶经》三篇,言茶之源流、饮法、茶具甚详,被后世奉为“茶神”。宋代出现茶户、茶市、茶坊。自此以后,饮茶风尚盛行。
唐代刘禹锡有首《尝茶》诗:“生怕芳丛鹰嘴牙,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品茗赏月,别有一番情趣。唐代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曰:“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七碗茶,尽赞茶叶质量之优良,描述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石碾轻飞瑟瑟尘,乳香烹出建溪春,世间绝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北宋诗人林逋的这首《茶》,明明自然之物,偏偏激起悠悠情思,品茗过程中的感官审美,揭示人们内心的生活感悟。南宋哲学家朱熹与茶结下不解之缘,以茶修身明德。有一次,他去游访上竺寺,同高僧品茗谈法,在寺壁上题了《春日游上竺》一诗:“竺国古招提,飞甍碧瓦齐。林深忘日午,山迥觉天低。琪树殊方色,珍禽别样啼。沙门有文畅,啜茗漫留题。”
元代刘秉忠的《尝云芝茶》诗云:“铁色皴皮带老霜,含英咀美入诗肠。舌根未得天真味,鼻观先通圣妙香。海上精华难品第,江南草木属寻常。待将肤腠侵微汗,毛骨生风六月凉。”句句写的是尝茶感受,却通篇不见“茶”字,令人有“经翻陆羽,歌记卢仝”之慨叹。
赵朴初也有首品茗诗:“七碗受至味,一壶保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喝茶去。”可见,喝茶不仅要有一份心情,而且要有一份较高的人生境界。其实,喝茶如同品人生,甘中有苦,苦中有甘,就看你是否以一份平常心去细细品它。茶品无穷,文章不尽;咏物抒情,相映生辉。
(责任编辑:寒江雪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