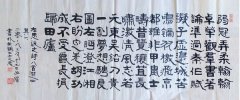中国书法艺术思考:写意释怀,生生不息(3)
书法研习与创造,都是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在这个活动过程,实践者释放性情,运化技艺,同条共贯着自己的那一个倾向性,究其根底乃是生命的润泽与智慧的开启,这需要不断积累与体验,具慧眼,找感觉,悟门道,是殊难或缺的要点,从实践流程看,这三个要点,是交叉与互动的,容略加分解。
俯仰古今,体察书法艺术意蕴,无论从宜,还是发现,自当不求功果圆满,但能寓赏存精,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倘在智慧之外美其名曰“创新”,在技巧和实用层次上可能带来某些功利效果,但智慧趣向并不归落在世俗功利上。势利化的智慧在向度上只能称为一种所谓的“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人一旦进入聪明圈套,那他的智慧的源头也就枯竭了,而本具有真正意义的艺术生命也就丧失了。的确,“目察秋毫之末者、视不能见太(泰)山,耳听清浊之调者,不闻雷霆之声。”会古通今,违险夷之情,体权变之道,非鼠目寸光者所能为。书法之美妙,犹“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惟具慧眼,才能悉其三昧。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何以“上”,何以“中”,何以“下”,靠的是“眼力”辨识。一个艺术家,没有形成一个独到的眼光,审视面临的一切,所做的将是平庸的。袁中道说的好:“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的确,有眼力,具智慧,才有可能出类拔萃。
书法艺术生生不息,所形成美的世界,鸾翔凤翥,云到雨施,有朝晖晚霞,有沧海桑田,涵泳着人的生命形态与情感冲动,统楫着阴阳、刚柔、虚实┄┄,无论面对过去,还是走向将来,都需要我们在捕捉或者发现、酝酿或者传达的过程中,将所把握的万千种感觉集于一念头之间吐纳,或为笔墨所役,“秋毫未合天地隔”,或敞开心扉,“真如天上落将军”。梦笔生花,乃妙手与妙眼所见的一刹间,找到了完美的契合。《兰亭序》因景生情,《祭侄稿》因事激怀,《黄州寒食诗帖》抒写心境,《韭花帖》小叙雅怀,在各自随机性的兴会搦毫中,那种种微妙感觉在心无芥蒂的流程中化解了。如果将他们各属于自己的那一种笔墨感觉,置于各自一生作品作比较考察,我们将会十分惊讶,尽管他们笔墨意味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变动或发展,但那感觉脉络中始终萦绕着一以贯之的独特标举的气息。历览书法大家大都如是,在“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兴会之时,产生许多意外。一个有所作为的书法家,必须涵育着具有鲜明个性的感觉,才有可能充分张扬自家趣向,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个感觉就可能铺衍出意外。在炼就慧眼,找到感觉的过程中,能否臻入佳境,悟出门道,是至关重要的。
弘一法师有一次在鹭岛南普陀寺谈书法,曾引用《法华经》一句话,并改了一个字,用之论述书法境界:“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法”改为“字”),在法师看来,世间无论那一种艺术,都是非思量分别所能解释的,离开思量分别才可以体悟,才能达到艺术最上乘境界。无怪他对僧众说“能十分学佛法,写的字也可以十分进步”,可不,“事境俱忘,千山万水,”“信有十分,疑有十分, 疑有十分,悟有十分,”门道何在,指向何方,全由你自己体悟。
戏剧界有傻把式,假把式,真把式之分,书坛亦类似。能写能悟,以至应目手熟,有了感觉,心精意会,别具慧眼,畅神觉醒,悟出门道,成了真把式,那明灿灿的书法世界,不就“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