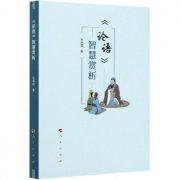“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
2010-05-07 09:58
来源:中国儒学网 作者:罗乐
有人说用恩德恩惠来回报仇怨怎么样,而孔子认为应该用直来回报仇怨,用恩德回报恩德。两者都基于一个“恕”的出发点。但是,在具体应对问题上,仍有着“度”的差别和区分。

《论语》中,“仁”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相较而言,孔子的另一个重要观点“直”却鲜有关注,特别是针对西方、老子“以德报怨”之学说,孔子实则早有“以直报怨”的观点可做回应。何者更加高明?此问题值得思索和探究。
在人与人交往和发展中,总会因为人趋利避害的本心,抑或利益分配的不公等诸多原因,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人情感情绪之一的“怨”随之产生,并与委屈,仇恨一类情绪相伴。随意翻开卷帙浩繁的人类史——征战,屠杀,歧视,诈骗,报复……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问题似乎从来都层出不穷,擢发难数。面对这样客观存在的矛盾冲突和主观存在的不满情绪,《论语》中提到孔子所认为值得倡导的应对方式。这段记载如下: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第十四》)
有人说用恩德恩惠来回报仇怨怎么样,而孔子认为应该用直来回报仇怨,用恩德回报恩德。其实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也分别被不同的人接受,并且两者都基于一个“恕”的出发点。但是,在具体应对问题上,仍有着“度”的差别和区分。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相较而言更具有它特别的意义和作用,出于以下的思考:首先,在孔子思想里,“直”有着怎样的意涵,“直”和“德”的关系如何?其次,用“直”来作为区分对待“怨”与“德”的原因为何?最后,用“直”来区分,重视“直”的意义为何?
一.《论语》之“直”
对于14.34章的解读,李泽厚认为:“这是重要的孔门思想,是儒学不同于那种‘报怨以德’(老子),‘舍身饲虎’(佛经),‘爱敌如友’,‘右脸被打,送上左脸’(《圣经》)等教义所在。也正是实用理性的充分表现。既不滥施感情,泛说博爱(这很难做到),也不否认人情,一切以利害为准则(如法家),而是理性渗入情感中,情感以理性为原则。在这里,儒家的社会性公德(正义公平)与宗教性私德(济世救人)又是合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李泽厚是把从老子与孔子,或者说中国儒教和西方宗教作对比,看待“直”与“德”的区分。区分的变量要素之一,就是何者更是“融入了理性的情感”。显而易见,得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结论。再追根溯源,根据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考证,最古老的天文仪器是一种构造简单的直杆——它立在地面,要求垂直中正。因此“直”很容易便和公正,中正联系起来,进而与“正”结合而成为一种品性,谓之“正直”。而再来看“德”。近代学者对殷代甲骨文以及西周初期金文的分析发现,“德”字是由“直”与“行”(或“行”的一半)构成。到了西周时期,“德”再添加了“心”符。所以“德”更倾向于感情博爱,因而把“以德报怨”与“滥施感情,泛说博爱”相联系。
而对于此问题,黄玉顺是从孔子观念的解读层面出发的。他认为如果根据孔子的观念层级来区分,“德”是道德礼法层级的事情,“怨”是生活情感层级的事情,两者不相对应。而“直”是出自于人本真的爱,才能和“怨”相对应,所以“应该‘以直报怨’、以情报情,亦即报之以本真的爱”
这两种出发点和区分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殊途同归的是:
第一,“以直报怨”中“直”出自于人的本心,出自于情感生活。正如钱穆概括“直”的意涵所提到的那样:“直者诚也。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心有所好恶而如实以出之者也。”而“孔子所谓直者,谓其有真心真意,而不以欺诈邪曲待人也。”也正因此,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第二,正是由于“直”发乎本心的特点,而人之性相近,因此兼具推而广之,由己及他而至众的特点。亦如钱穆所言,“以直报怨者,其实则犹以仁道报怨也,以人与人相处之公道报怨也。”以直释仁,也是诸多学者的共识,不再赘言。
如若结合周遭现实问题——恐怖分子肆意猖獗的袭击活动,种种比天灾更可怕的惨绝人寰的人祸:仇恨,屠杀,战争,歧视……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敌对和问题,需要思考:普罗大众可以,或者说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应对?即便我们没有真正身陷强烈的纷争,也不妨自忖,面对激烈程度相对较低更切身的现实问题现实仇怨,抑或说如果我们真的不幸成为受害人或者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犹太人的后裔,911恐怖袭击罹难者的家人,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目击者和幸存者等等。承载着这些历史的创伤和仇恨的人们,又该怎样应对,如何去“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