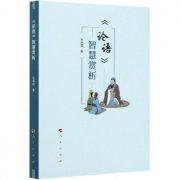“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3)
2010-05-07 09:58
来源:中国儒学网 作者:罗乐
这两章是孔子对于具体的人事判断,阐述直是出自于本心真诚,无私无偏,不刻意为之的特征。结合前两章可以看出,用直这种源自于本心,真诚而率性的
这两章是孔子对于具体的人事判断,阐述“直”是出自于本心真诚,无私无偏,不刻意为之的特征。结合前两章可以看出,用“直”这种源自于本心,真诚而率性的认知态度,来直面问题与冲突,区分德怨,体现了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
孔子亦重视“恕”。即便是“以直报怨”,也和“以德报怨”的这个基本出发点是一致的。所以明确的是,直可以与“公正”“公平”一类挂钩,只是确定态度和区分度,不包含行为上的方向性暗示。如果我们妄加揣测,借题发挥,用一个“直”来作为下一步行为报复的合理跳板,是有违本义的。
孔子对于他的时代问题从来都是有明确的好恶是非观,也不认同所谓的“人皆爱之”“人皆恶之”的人群。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认同与共鸣。朱子认为,“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于其所德者,则必以德报之,不可忘也。”他看重“德”与“德”相对应,用“不可相忘”来自勉,身体力行。而钱穆本人身处近现代社会,亦说:“人虽与我有私怨,我未尝以我之私怨而报之,直以人与人相处之公道处之而已。公道即直道也。若人有怨于我,而我故报之以德,是未免流于邪枉虚伪,于仁为远,故孔子不取。或曰:‘直道非一,视吾心何如耳。吾心有怨,报之,直也。苟能忘怨而不报,亦直也。惟含忍匿怨,虽终至不报,然其于世,必以浮道相与,一无所用其情者。亦何取哉?’”他眼里直道是关乎个人本心的,只是个人行为的参考前提而不是决策方向。钱穆的这一观点十分明确。对于社会层面的问题解释同样简明扼要,鞭辟入里。他说:“人类之生存于世,端赖其以直心直道相处。至于欺诈虚伪之风既盛,则其群必衰乱,必败亡;其得免焉者,幸也。罔即专务自欺以欺人者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
可以看到,“直”的确立,无论对于个人情感的去留,还是对于社会性问题的解决,抑恶扬善,抑或社会性公德的巩固都是有实质意义和作用的。
如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放诸解释文章第一部分尾部提到的问题,即当今社会中的冲突和纷争——无论是惊人的恐怖报复袭击还是恼人的人际纠纷积怨——都是意涵斐然。
正如简括前面探讨说明的,《论语》中的“直”既有出乎本心的合情性,又有推而广之的合理性;既有区分“德”与“怨”的理论作用,又有“矫枉”的实际效用;既可以指导个人情感,又可以维系社会性公德。可能我们人类的问题注定层出不穷,纷争不断,所以人类本身面对问题,选取的态度和姿态几乎可以决定问题的去留和生存的方向。我们可能难以找出很多矛盾的真正解决办法——如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宗教战争似乎难断是非,艾滋病毒的传播仍带来问题重重,科技带来福祉似乎也造成灾难等等。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先找到应对矛盾时候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尺度——那就是,面对基本的恩德和仇恨,即便我们的应对行为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牵扯而错综复杂,但是至少可以确立的是——我们首先可以,并且有必要进行一个应对态度上的区分。这就是《论语》中“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最为值得重视的意涵。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