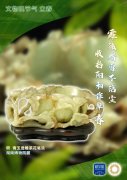景教碑历险记(上)(3)
从何乐模前期筹措经费和与各界人士的接触、商讨过程来看,他实际上是怀着一种做买卖的生意人心态,先筹募“历险”的本钱,期待着获得景教碑或者仿刻碑之后,再以高价出售给某个西方博物馆,从而谋取较高的利润,实现“名利双收”的目的。
1907年3月12日,何乐模从纽约中央车站乘火车北上,首先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再换乘横跨加拿大的长途列车奔赴太平洋东岸的温哥华,由此搭乘“印度皇后号”邮轮横渡太平洋,抵达日本横滨港,由此乘火车前往神户,再换乘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芝罘号”邮轮,经长崎,在绕行了大半个地球后,于4月10日抵达天津。何乐模这次入华的万里行程,先后途经欧洲、北美和东亚,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历时60余天。
何乐模入住天津著名的利顺德饭店后,随即为前往西北内陆的西安城做各项准备工作。他首先前往北京外务部办理前往内地游历的护照等手续,在当时代管丹麦国民在华事务的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护照。曾在西北内陆和蒙藏地区进行过深入考察的美国驻华公使、大名鼎鼎的探险家柔克义还向何乐模传授了在内地旅行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何乐模”这一中文名字的来历。在众多中文史志、论著中,往往将Holm音译为赫尔姆、霍尔默、何尔谟、荷尔谟、好尔姆、呼伦等多个名字,容易令人混淆。而事实上,何乐模于1907年从伦敦经哥本哈根、纽约、温哥华等地来华后,北京的清廷外务部颁发给他的护照与其个人使用的名帖上均标有中文姓名“何乐模”。根据他在1909年《帕特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记述,这一名字是由清廷外务部官员将他的英文姓氏雅化后所取,意指“何等悠乐之楷模”,令他大为满意。
从北京回到天津后,何乐模经人介绍雇用了一名祖籍宁波的翻译方贤昌,此人曾供职于京奉铁路,会讲英语和法语;另外还雇了一名略通德语的仆从马四。何乐模为了防止两名随员互相串通欺骗自己,就分别用法语和德语与两人交流,这样一来,交流的内容也就不会被另外一人知晓。而一路上方贤昌和马四两人关系并不融洽,这反倒免却了何乐模的所谓“担忧”。但后来也正是方翻译在敦促陕西地方官府把景教碑移入碑林,防止外国人破坏或者盗运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
“掩耳盗铃”的隐秘活动
1907年5月2日,何乐模一行三人坐船离开天津。与以往从京、津前往西北内陆的大多数西方人走保定、太原、潼关、西安的传统大道不同,何乐模为深入考察华北、西北各地自然与人文景观,选择了先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过直隶静海县、唐官屯、流河镇、新河县、东泊头等地;5月7日入山东境,经桑家园、德州、武城、临清州;由此从卫河航道上行入河南境,经高地镇、五陵、三官庙、浚县,终抵道口火车站。此后何乐模一行从道口乘火车南下至铁路终点站清化镇。再租雇大车,经怀庆府,过黄河抵达洛阳,而后从洛阳向西安进发。5月29日入潼关,6月3日进入西安城。此行途经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四省区,交通工具包括船只、火车、大车、骑骡等,也颇为多样化。
何乐模从1907年6月3日进入西安城,至6月29日离开,第一次驻留西安城为期26天。
何乐模在到达西安城之初,即依照惯例接受陕西省洋务局等机构查验护照,并向陕西巡抚曹鸿勋以及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递交名帖,登门拜会,但始终没有透露此行的真实目的,而是扮做普通西方记者(名帖上标明为“大丹国文士”)四处游览,先后参观了大雁塔、碑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行宫、临潼华清池等地。他假装采集素材,实则暗中了解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仿刻碑的可行性。同时,他还与当时居住西安的西方人积极接洽,希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帮助。他和两名随员不仅入住西安邮政局德国籍局长邵穆劳菲尔位于西北城区的阔大宅邸之中,还与天主教会、英国浸礼会、中国内地会系的北美瑞挪会等传教士密切接触,多有往来。在抵达西安之初,何乐模就在五星街天主教堂的主教和神父们陪同下前往高陵通远坊教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徒纪念日活动。
在与当时西安城的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何乐模向他们隐约透露出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一通精准的仿刻碑的计划,但这些西方人实际上对他的计划并不支持,甚至有反对的声音。这是由于天主教会也曾有将景教碑运往罗马的计划,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出于景教碑碑文与基督教相关,认为新教教会对该碑至少应有部分的所有权,对何乐模以私人身份获取原碑的目的有所诟病,这从后来新教传教士在汉口、上海、天津等地报刊上发表的揭露何乐模隐秘行径的文章中也可看出。
1907年6月10日,何乐模骑马出城,首次前往金胜寺实地考察了景教碑。当时正是关中麦收时节,何乐模在围绕着景教碑来回踏勘、拍照、绘图、留影之际,金胜寺的僧人和周边农民们依然在地里忙着收割小麦,并没有在他做这些事情时加以干涉,但何乐模也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景教碑就是一通无主之物,可以任由搬运。由于在较早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已经有关于景教碑地点的详细位置记述和草图,因而何乐模按图索骥,很容易就找到了矗立在金胜寺麦地中的景教碑。
“贿赂”中国和尚
为了找到获取景教碑原碑的捷径,何乐模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与金胜寺住持、74岁的玉秀和尚建立了联系,先后向玉秀赠送丝绸、放大镜等小礼物。当然,何乐模自己都承认用“贿赂”一词形容送小礼品的行为未免有些名不符实。从何乐模本人的记述中看,他虽然提出过把景教碑原碑搬走的要求,但玉秀坚持认为景教碑属于金胜寺和他个人,从来没有与何乐模签订坊间传言甚广的所谓“秘密契约”出卖景教碑。关于何乐模与玉秀之间的交往,1935年刊行的《续修陕西通志稿》载何乐模“以重(金)贿赂僧”,1936年刊行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更具体载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丹麦人何尔谟出三千金购之”,后来的论著往往就笼而统之地称何乐模向玉秀出3000两白银,想购买景教碑。虽然从现有资料和照片来看,玉秀和尚与何乐模的关系较为融洽,何乐模还为玉秀在金胜寺和景教碑附近拍摄了多帧照片,但却远不能说明两人之间订立有出售景教碑的契约。这一说法大概是受到了斯坦因在敦煌向王道士低价购买敦煌经卷一事的影响,殊不知人烟稠密的西安并非僻远闭塞的敦煌,而坚守金胜寺50余年的玉秀和尚也并非愚昧贪财的王道士。
从何乐模本人撰写的大量文章、著作,以及当时英、法文报刊记述的情况分析,玉秀与何乐模签订的唯一“契约”是出租寺庙中两间房屋的约定,其中一间用于石匠仿刻景教碑,另一间供翻译方贤昌居住,以便就近监督工匠的工作。两间屋子四个月的租金为50两银子(约35美元)。对于何乐模这样一个“中国通”来说,他不会不知道住持和尚实际上并非阻止他获取景教碑的最大障碍,即使用3000两银子买通了住持,要想从位于西安前往咸阳、户县的两条东西大道旁边的金胜寺运走2吨重的石碑,而不被官府和民众发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自从何乐模抵达西安,他自认为行踪秘密,实际上由于当时往来西安城的西方人较少,他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处于陕西洋务局官员的视线之内。何乐模灰心丧气地称,要想从西安把原始的景教碑不为人知地运走,就好像从大英博物馆运走罗塞塔石碑,或者从卢浮宫运走摩押碑一样,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