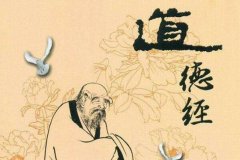从《庄子》看齐文化(4)
2010-06-10 11:22
来源:文史哲 作者:蔡德贵
《说剑》说: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显然与齐人甘德《
《说剑》说:“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显然与齐人甘德《天文星占》中所说的“天圆地方”学说是一致的。
《庄子》一书先后提到许多稷下先生,《逍遥游》中的宋荣子,即宋鈃,《则阳》中提倡莫为的季真,提倡或使的接子,都是稷下先生。“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或之使,莫之为,疑之所假,”“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使”,“或使莫为,在物一曲”,这些思想学说,《庄子》一书是保存得最这完整的。《天下》篇中叙述天下方术,更是集中论述了宋鈃、尹文、彭蒙、田骈、慎到诸多稷下先生的学说。庄子对稷下学者这样熟悉,这就难英国科学史巨匠李约瑟博士曾认为庄子本人可能也是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
然后,我们还可以从庄子对海的认识看出他和齐文化的渊源。我们知道,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但大多数时间是在鲁国。他到过齐国,但居留时间甚短,一部《论语》,只有一处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可见,孔子是在周礼行不通的情况下才想飘洋过海的。孟子在齐国居留时间比孔子长,对海的感触也很深刻。《孟子》一书提到海的地方有9次,孟子体会最深的一句话是“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尽心上》)。再看看齐国人的庄子,简直对海的习性非常熟悉了,北冥、北海、南海,都是经常提到的。《应帝王》说“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徐无鬼》说“故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逍遥游》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更有《秋水》中所说的河伯与北海,描写河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而北海则是“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北海之神若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对海进行这样深入细致地描写,如果不熟悉大海的习性,仅凭想象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庄子是齐国人。
这就足以证明沿海文化哺育了庄子,庄子是沿海文化的产儿,庄子与齐文化之间,就是这样一种永远也撕扯不开的联系。
最后,再看庄子思想的本质特色。《庄子》一书包含有这样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是否全书就没有主线了呢?应该说,主线还是有的,这就是贯穿全书的全性说和贵齐说。
《荀子·解蔽》在评论庄子时,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只知因任自然,反对人为。《庄子·秋水》说:“牛马四足是为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又说:“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乎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所以,提倡“无以人灭天,无以故(人为)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要人保全天然的本性,顺性而为,而反对对本性的戕害,违反自然本性而妄有作为,只会导致可悲的下场。《庄帝王》中为浑沌凿窍的故事就是证明。
但是,人生在世,要遇到许多麻烦,会干扰人保全真性,为此,庄子用养生说和贵齐说来完善他的全性说。养生说出于人的自然天性的考虑,因为性是天然生成的,因此“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天运》),“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谓之伪,谓之失”(《庚桑楚》)。人的生命是自然天成的,要尊重生命,“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让王》)。养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精神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要达到精神的自由,就必须摆脱感官的牵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在宥》)。精神上自由了,就可以超越生死的束缚,达到理想的最高境界。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可以超越“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的古之真人,成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的“真人”(《大宗师》)。可以说,养生说是庄子对自然无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