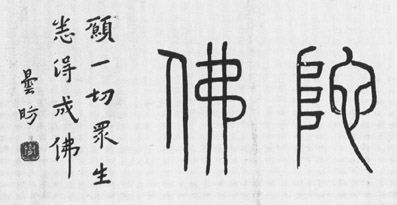水墨山水画境界高远,格调高华
 中国艺术向来以境界论高下,境界理是中国山水画品评的终极指归。古往今来的山水画大家的作品莫不是境界高远、气韵风发、格调高华,像一座座岸峻拔、威震云汉的巨峰巍然群立于华夏大地上,引领后人高山仰止。山水画之所以不同于风景画,其中心关捩在于艺术境界的抉微与诉诸,这种对境界的自觉追求显然来至滥觞于先秦时代士人们的山水、自然观。可以说,自山水画诞生起,“以形媚道”便成为山水画创作的精神指向,山水画已然承担起“含道映物”、“澄怀味象”的形上使命,从而与风景画拉开距离,山水画的艺术境界由此而彰显,山水画的审美功能也由此而升华。
中国艺术向来以境界论高下,境界理是中国山水画品评的终极指归。古往今来的山水画大家的作品莫不是境界高远、气韵风发、格调高华,像一座座岸峻拔、威震云汉的巨峰巍然群立于华夏大地上,引领后人高山仰止。山水画之所以不同于风景画,其中心关捩在于艺术境界的抉微与诉诸,这种对境界的自觉追求显然来至滥觞于先秦时代士人们的山水、自然观。可以说,自山水画诞生起,“以形媚道”便成为山水画创作的精神指向,山水画已然承担起“含道映物”、“澄怀味象”的形上使命,从而与风景画拉开距离,山水画的艺术境界由此而彰显,山水画的审美功能也由此而升华。
当下山水画创作大有向风景画滑落的趋势,画家们往往只注重刻画山水形貌的真切精微,强调形象的逼真,而笔墨、意境、气韵渐趋式微,可读性差强人意,更谈不上耐读了,艺术境界平薄、庸俗,山水精神的文脉渐趋扼断。因此,提升山水画艺术境界是当下山水画家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那么,如何提升山水画的艺术境界呢?我以为,不妨由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言境一 极笔墨之美性,氤氲生动,浑厚华滋
如同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一样,笔墨亦是中国画的母语,是国画“国”画的根本和灵魂,舍弃笔墨无异于断送国画赖以生存的命脉。 经过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笔墨自身已然是一个特定的生命的文化机体,因此它不存在着新与旧的问题,只有好与坏、高与低、雅与俗的界域,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形式要向前走,而笔墨不妨向后看。我很同意郎绍君先生的观点,即传统的笔墨语言“高度成熟与完美,不存 在‘转型’和‘现代化’的问题”。所以对于笔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认知并且把握其生命构成规律,这才是传承和发展国画文脉的根本所在。事实上,再完美的传统语言都有“再生”的力量和可能,关键在于画家于笔墨修能的过程中,能否将才情、学养、思想等艺术质素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笔墨中去?能渗透进去,笔墨便具有了自我的人格美性,如此,笔墨语言便有了独特的个性与魅力。如果没有渗透进去,最终只是在重复前人的笔墨程式,那么,这样的笔墨就缺乏生命力,也就谈不上出新和再生了。石涛讲“法不执能”,就是说,传统法则对于“能”者来说,不但没有束缚,反而能增强创新的底气与活力,所谓“天授授予可授之人”。
在‘转型’和‘现代化’的问题”。所以对于笔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认知并且把握其生命构成规律,这才是传承和发展国画文脉的根本所在。事实上,再完美的传统语言都有“再生”的力量和可能,关键在于画家于笔墨修能的过程中,能否将才情、学养、思想等艺术质素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笔墨中去?能渗透进去,笔墨便具有了自我的人格美性,如此,笔墨语言便有了独特的个性与魅力。如果没有渗透进去,最终只是在重复前人的笔墨程式,那么,这样的笔墨就缺乏生命力,也就谈不上出新和再生了。石涛讲“法不执能”,就是说,传统法则对于“能”者来说,不但没有束缚,反而能增强创新的底气与活力,所谓“天授授予可授之人”。
笔墨文脉固然要通过大量临摹前人名家名作来窥其精要,这是一条无可回避的途径,其实也是一条捷径。同时,更要加强书法的学习,因为,笔墨归根结底是落实在笔法上的,郭若虚说:“气韵本乎有心,神韵生于用笔”;黄宾虹在《画法要旨》中也讲到:“论用笔法,必兼墨法之妙,全从笔出。”因为用笔之道,关捩在于用笔的“书写性”,即《六法》中的“骨法用笔”。所以,强化书法训练是提高笔法质量的有力保证。更重要的是,书法是最能够体现作者人格、情性的自我独立与完善,是彰显笔墨个性化、人格化的重要基础。纵横上下,凡山水大家其书法造诣无不精妙绝伦,个中消息,粲然在目。总而言之,笔墨美性的诉诸尽在用笔之中,运用之妙,存乎一笔,千笔万笔始于一笔又终于一笔。得此一笔,浑厚华滋;了此一笔,氤氲生动,笔墨境界由此昭彰。
物境一 极丘壑之内美,风化幽微,可读可游
自然山水是山水画的载体,是“媚道"的形,完全无视形的表现,只眈眈于笔墨语言,这是游戏,更是习气,不足取。古人云:“山水质有而趣灵”,画山水“质有”了,才能反映出山水的“趣灵"来,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王维说“肇自然之性”,就是以自然为本、以自然为依据,而能“成造化之功”。当下有些山水画家为了标举“个性”,张扬“风格”,从而为“形式”而形 式,不惜放弃对山水本体意义的深沉探索,致使山水成为纯粹的抽象符号,而山水固有的自然之气和生命魂魄渐趋丧失,这无疑是一种盲区,是极不正常的,也是悖逆艺术规律的。没有形的依托,山水之美何能呈现?这一点需要正本清源,“夫画,本乎形者融灵”(王微《叙画》)。山水画唯有了“形”“质”,才能使观者“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宗炳画山水序》)。
式,不惜放弃对山水本体意义的深沉探索,致使山水成为纯粹的抽象符号,而山水固有的自然之气和生命魂魄渐趋丧失,这无疑是一种盲区,是极不正常的,也是悖逆艺术规律的。没有形的依托,山水之美何能呈现?这一点需要正本清源,“夫画,本乎形者融灵”(王微《叙画》)。山水画唯有了“形”“质”,才能使观者“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宗炳画山水序》)。
当然,一味忠实于山水形貌的精雕细琢,成为“自然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徒取形影是难以达到艺术高境界的。山水画以追求“山水内美”为上,也就是说要充分揭示自然山水 的精神实质,这样才能“由自然之景而进入艺术之境”,比如画青城山,要在“幽”字上着力;画峨眉山,要在“秀”字上用心。如何将自然山水“转换”升为笔下山水、心中山水?是一个山水画家需要不断修持的课程。眼里只有自然山水,是无视我的存在;眼里没有自然山水,是无视物的存在;只有融我与物,主客观高度统一,才能进入天人合一的超迈境界。具象、抽象都有其极限,唯有意象,它的空间是广阔无限的、没有边际的,所谓“物境”就体现在这里。